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投票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该法案的前身之一《无尽前沿法案》,此前因致力于扩大高科技领域的研发投入、保持对中国的科技竞争优势而备受瞩目。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关键要素,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已经成为各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国家科学”形态基本成型。面对“国家科学”时代的来临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如何应对?
“国家科学”时代的形成
什么是“国家科学”?首先,国家作为战略科技力量的需求方,顺理成章地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成为战略高科技的主要投资人。
其次,“国家科学”不以解决单项任务、取得局部进展为目标,而是追求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战略高科技的整体突破,重视科技转化的路径和效率,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建构。
其三,在当前“国家科学”战略目标之下的前沿高科技领域,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经常难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并且“基础”与“应用”时常互为对方之母,量子科技、人工智能、核能等领域都是如此。因此,从逻辑上说,“国家科学”会淡化战略高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分,仅以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科学”并不必然地与“自由研究”产生冲突。
1990年代,美国政府先后发布了《科学与国家利益》《技术与国家利益》两份政策报告,确定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国家利益导向。根据这种政策导向,美国国会要求国家科学基金会审查项目时必须考虑项目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拉开了“国家科学”的序幕。
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向国会提交了《无尽前沿法案》,提请国会通过法案,大幅增加国家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和制造等关键技术的研发资助(5年拨款1000亿美元)。
《无尽前沿法案》在美国参议院经过1年多的辩论、近20次的修订补充、综合各方利益后,形成了指向性更明确、范围更广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其中包括6个部分:芯片和5G通信紧急拨款法案、无尽前沿法案、战略竞争法案、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规定、应对中国挑战法案,以及其他事务(包括教育和医学研究的竞争力和安全性)。法案提议的拨款金额也从最初的1000亿美元增加到2500亿美元。
《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全文1445页。该法案的提出、陈述、辩论、补充及最后定稿实施,或将成为“国家科学”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应对之策
为了应对国际科技创新战略博弈和争夺科技制高点,我国科技发展也朝着 “国家科学”的方向调整,已有以下表现形式和特征: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化国家战略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21—2035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以及“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等的制定和实施是几个具体实例。
强化科研选题的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要求基础研究应用牵引、突破瓶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
资源配置越来越倾向于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领域,如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设置等。
科学活动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体现国家力量的介入,如布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等。
科技奖励和激励机制越来越体现服务国家发展、围绕国家战略全局的基本原则,如《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2017)的制定,以及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高调布局等。
亟待解决的问题
毋庸讳言,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与“国家科学”时代不适应、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首先是科技评价问题。
最近30多年来,SCI论文数量在职称、学位、评奖、基金项目申请、课题成果鉴定等方面被赋予了突出权重。我国80%以上的优秀科研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在各种需要评判学术水平的场合,不得不“客观地”考查英文期刊和英文文章,主要依从国外的评价体系。假手他人的结果是加重优秀论文外流,加重科研价值观的偏差,也是学风问题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本原因。
科技评价假手他人、以文献计量代替整个科研评价的状态应该迅速纠正。与“国家科学”时代战略要求相符的综合学术评价体系至少应该包括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学术贡献指标、专业能力指标和社会影响指标。
其次是科技数据话语权问题。
优秀学术论文的外流以及数字出版平台的羸弱,不仅使我们难以掌握学术评价话语权,也让我们损失了大量优质数字资源,从而丧失了科技数据话语权,使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受到严重威胁。
建议从科研论文着手,与科技评价体系建设配套进行有国际竞争力的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
再次是战略协同性问题。
战略协同性在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全球技术标准话语权争夺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科学”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在“国家科学”时代,提高战略协同性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这应该成为我们制度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地方。
战略实施甚至比战略制定更加重要。在具体实施方面,《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确有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地方,它对战略实施的目标、措施、路径、责任人都有非常明确细致的规定,这也是它篇幅巨大的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曾有举全国之力在重大科技工程和“卡脖子”项目上取得成功突破的诸多个案,如“两弹一星”工程等。在“国家科学”时代,我们不能心存幻想,指望我们曾经熟悉的国际科技与合作秩序、国际产业链分工协作机制能很快回归;也不能在我们市场机制还相对弱小的战略领域投鼠忌器,错失举国体制发挥作用、改变被动局面的良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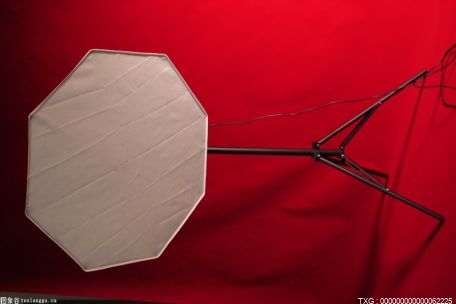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